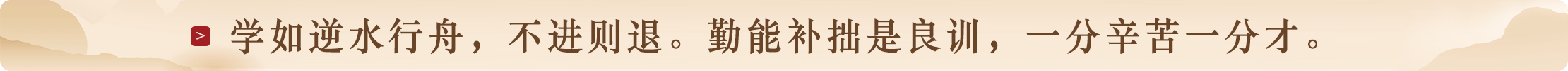来源|谷雨星球ID|guyujihua2026作者| Summer夏景大家好,我是莎莫Summer,谷雨星球的创始人。上个月的美国大学发榜季,我们发现早申放榜,但喜报少了:国际教育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这样的变化会在英国名校重现吗?连夜整理完牛津2026年预录取数据后,情况好像很不一样。昨晚,牛津发出了最新的录取信,共计167枚(预)录取,比去年的近180枚有所减少。一方面因为人数的减少,UCAS数据显示,今年是牛剑申请者人数连续下滑的第三年,牛津申请人数减少了2.6%。然而,竞争难度没有下降。
数据不仅反映客观事实,还能在喧嚣的信息之中,提供相对冷静的视角:
中国是牛津的第一大海外来源地,每年大陆申请人数2000人左右,平均最终入学165人,几乎与美国八所藤校在国内录取人数持平。
牛津是分控,最看重成绩,但与刻板印象「洋高考」不同,学术综合能力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超纲Super-Curricular。
不管读国际高中、培训机构或自学都能申请牛津,还出现不少全日制机构,在国际教育疯狂追捧状元化的风潮下,目标就是提分的机构越发成为刚需。
再深挖一点,数据想告诉我们的真相,远不止这些。牛津大学官方数据显示,2026-2026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者为6558人,最终入学人数为500人。据已有数据可知,牛津大学今年发出167枚录取,与去年有所减少,属于正常范畴。备注:科桥是培训机构渊学通旗下的全日制教育机构,目前无法得知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几个要点,有的跟去年类似,有的则完全不同:1、TOP10学校出炉!这些年来,TOP10学校越来越固定,几乎很少易主,只有顺序的变化,牛娃集群效应凸显。不难看出,深国交始终屹立群雄之巅,且随着学校体量的扩大,年年录取人数再传巅峰。跟以往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第二名变成了上中国际,而非老牌A Level 学校,越来越多牛娃加入战场,TOP5的4席都被上海占了。与去年有些不同的是,我也能感受到申请的理性回归。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对于英美大学的差异了解得越来越多,学生们也早早选定方向,竭尽全力。UCAS数据显示,中国申请者比去年下跌。2、民办占比最多,IB/AP入局,机构成刚需英国顶尖大学的录取几乎都分布在民办学校,占比67%。A Level学校仍旧强势,不过势头比前几年霸屏时有所下降,占比刚过一半,AP学生增幅非常大,其次是IB。同时,课程分布也跟城市有关,一线城市的学校课程相对多元,二三线城市以A Level为主。不过也提醒大家,千万别用牛剑等英国大学申请榜来判断一所IB或AP学校的优劣,因为申请牛剑的基数可能不大。牛津申请还有个不大一样的地方,因为其不看学生在学校的相对排名,只看绝对分值,学生可以自学去考A Level(很多机构都有授权),或者去机构培训,都能申请英国大学,灵活性很高。由此,开设A Level的全日制机构和民办培训机构资质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了,因为培训机构容纳的体量大,且目标相对单一,只要负责出分即可,有的机构能拿下几十枚牛津录取,如唯寻。同时,随着越来越多非A Level牛娃申请牛剑,许多美国方向的机构也随之入局,战绩不俗。3、上海是牛津最爱的城市从省份城市来看,上海广东孩子更偏爱申请英国,尤其是上海,汇集了长三角申请牛剑的牛娃们;深国交甚至是吸纳着全国的优质生源。今年的平和、世外、包玉刚、上中国际、WLSA等都交出了非常好的答卷。尤其是今年,上海逆风上扬,成为了牛津最好的城市,拿下近70枚录取。而广东整体有所下降,北京持平。这个数据与申请系统UCAS也呼应上了——英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里,光上海一地就占了13%。北京学生相对倾向申请藤校等顶尖名校,TOP30申请和录取人数都比上海和广东多出不少。4、专业选择更倾向回到理工科从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大家所读的专业仍以中国学生擅长、牛津也扎实的理工科为主,跟往年比,占比更多了。但是另一方面,有些硬核的文科专业也有中国学生申请上了,如英文文学、古典学和惠灵顿的法学。再如关注全人教育的耀华集团旗下的上海耀华临港和广州耀华各收获了1枚,其中一枚还是录取率极低的纯艺专业。专业没有往年录取多元,原因有申请人数的下降,也跟录取率相关。牛津的录取大致分为三种:无条件录取、有条件录取和开放录取。A Level和IB的大考都在今年的5月份,所以拿到有条件录取的同学必须满足学校的分数要求,比如IB总分不能低于42分,并且某门学科必须拿到满分。牛剑申请流程大致为提交材料——入学考试的笔试——提交文书——面试——发出预录取——满足转正学术条件拿到正式录取——入学就读或无法转正。牛津的平均面邀率为30%,从面邀到预录取的平均为9%。那么,从预录取到录取的概率有多高呢?牛津官方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牛津收到23819份申请,发出3645份预录取,最终入学学生人数为3271,有374名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入学,比例超过了10%。也就是说,100个人中,就有10个学生最终没能入学。随着信息的普及,众所周知,英国大学录取就看成绩,但跟往年比,今年在以往的标准上又有了些新策略。其一,分控!分控!超分控!英国顶尖大学最为看重的就是学术成绩。学校官网非常明确规定了学生的入学门槛,没有达到分数线则免谈,跟国内高考有些像,所以也被称为「洋高考」。牛津剑桥会有多次面试,但跟美国面试「侃大山」不同,题目也是围绕申请专业的学术问题或学生提交的学术兴趣而展开。有一项宝藏数据,牛津公布了近三年共517位中国录取者的成绩,我们全看了一遍,并做了个统计:A-Level学生占比61.7%,其中35.7%拿到3门A*,29.2%4 门 A*,超过3/5的学生都拿到了3A*以上;
IB学生占比22.8%,86%的学生得分42+,37.7%是IB满分;
AP学生占比16%,36.1%的学生提交了4门AP满分,最高记录是11门AP5分。
其二,笔试、面试后综合评估申请进入不同的专业,要考不同的笔试,且难度逐年提升,高分也是中国学生的代名词。以热门的数学系为例,中国录取学生数学与计算机专业MAT均分最高,达到86.25;数学专业次之,MAT均分为83.59,数学与哲学专业、计算机科学专业MAT均分在77+。今年还有一项重大变化,牛津所有专业的申请门槛都达到更高水平,雅思总分7.5,单项7.0;托福总分110,听力22、阅读24、口语25、写作24。虽然申请人数有所起伏,但牛津并没有放宽入学门槛,反而更加严苛,中国学生本身的实力也让录取分数线整体上移。因为牛津是个超分控,所以如果面试发挥不是特别出彩,但笔试成绩特别高也不用担心,最终是将所有材料进行综合评估,决定录取名单。坊间一个说法:笔试型学生首选牛津、面试型学生首选剑桥,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三,Super Curricular能力更重要牛津作为全球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开设本科专业大多是3年,4年就能读完本硕,学术压力不小。而且,入学后不能转专业,也不能选课,几乎没有缓冲期、没有过渡期,直接浸润到所在专业的深度学习,高强度学习围绕本专业,且假期里进行专业相关的实习或实验室研究,一条路走到底。牛津培养的是专才,自然不是只会做题的书呆子,而是有着应用能力和学术研究潜力的同学,有个词叫Super Curricular,指的就是跟学术兴趣相关的课外拓展能力。很多学生会陷入一个误区:只要用这些高光装点自己的履历,就能打动招生官,更重要的是对专业的熟稔程度、对学术的批判性思维,对于能力的提高,对于用学科思维去改变世界的专注等。能力比形式更重要,比如深度阅读或许比打竞赛更含金量。要培养这些能力,不仅需要学生能高效完成校内功课拿到高分,还得有时间去做超出校内的研究和思考。而这种综合实力的考察又与美国大学申请靠拢,所以一些学校英美同申的牛娃通吃。牛津官网上有许多Super Curricular的资源。我们为每个上名校的孩子而感到自豪,也鼓励追求好大学,少年少年立志,资源眼界同伴定能让孩子收获良多,我自己也是优质教育的受益者。牛津学生告诉我,她最喜欢的就是学校里全球最古老的图书馆,走在校园里仿佛穿越历史。学校所带给她的浸润,与专业领域顶尖教授的交往,与优秀同学的志趣相同等,都是极为珍贵的财富。但我们却极度反对内卷。在几千申请者中,能拿到这封录取的寥寥无几。可惜的是,在当下国际教育状元化的市场里,眼里只有那些最顶尖名校才算是实现了升学上的成功,为越来越窄的独木桥榜单而变得焦虑。经济学许多研究都发现,当过了学历门槛线后,一个梯队学校为未来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差无几,投入边际效应几乎为0,乃至负增长。前几天,我们分享了一篇故事:收到牛津的拒信,我努力了18年的求学,失败了吗?她在一开始的崩溃不解到反思和解打动了无数人。她说,光是做出申请牛津这个决定,我就已经收获了许多珍贵的经历,而如果我没有勇敢地去尝试,我现在也还在舒适区里。被牛津拒绝并没有使我退步,而准备牛津申请的过程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这何尝不是教育的真正价值所在呢?更重要的是,在一阵阵发榜的喧嚣中,她意识到:「在申请中,若太过于关注他人的成功,就越难摆脱对失败的恐惧;若太过于关注学校头顶的光环,就越难清晰地审视自身。」而这些看起来都是简单的道理,在国际教育状元化的当下,我都得一遍一遍反复提醒自己,如同逆水行舟,才能勉强做到。MVP学习网授权转载自“谷雨星球”邀你一起做内卷下的教育长期主义者